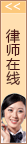房屋交易已交付但未登記情形下繼承標的之辨析
來源:上海房產律師網 作者:上海律師 時間:2022-08-18
房屋交易已交付但未登記情形下繼承標的之辨析
——馮某戊訴馮某乙、馮某丙等
繼承糾紛案
案例摘要
本案系因房屋交易已交付但未登記情形下引發的繼承糾紛,案件涉及繼承標的辨析、不動產物權變動、合同債權承繼與履行以及合同債權在繼承糾紛中處理等多項法律問題。在“物權說”與“債權說”的博弈中,本案裁判對不動產登記在繼承標的界定中的作用予以明確,在確定除與被繼承人人身有關的專屬性債權或合同特別約定不得繼承的債權外、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其他合法債權可作為遺產進行繼承這一裁判規則的同時,提出繼承糾紛考慮案件具體事實,從便利訴訟角度出發,可以對合同履行與遺產繼承一體化處理的裁判思路。
關鍵詞
繼承標的
物權變動
合同債權
遺產范圍
裁判要旨
1. 不動產登記的目的在于對不動產物權的得喪變更進行公示,其雖然可以進行真實物權人的“權利推定”,但并不能片面作為“權屬確認”的依據。
2.我國不動產物權變動同時需要法律行為和依法登記,雙重法律事實決定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效力。若僅具有當事人之間的原因行為,而未完成登記,則相應的物權變動因欠缺生效要件而未發生物權效力。
3.除與被繼承人人身有關的專屬性債權或合同特別約定不得繼承的債權外,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其他合法債權可作為遺產進行繼承。繼承糾紛中考慮案件具體事實,從便利訴訟角度出發,可以對合同履行與遺產繼承一體化處理。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
基本案情
馮某戊訴稱:2002年因母親馬某原房屋拆遷,子女五人及母親共同協商,由馬某購買馮某乙810號房屋,并支付購房款30萬元,馮某乙出具手寫收據。隨即馬某與共同居住的馮某甲長子馮某己一起入住810號房屋。后馮某乙以多種理由拖延辦理房屋過戶手續,直至2010年馬某去世一直未能辦理。故主張:1.依法確認涉案房屋是母親的遺產,由子女五人按照每人20%的份額繼承;2.馮某乙將其名下屬于母親遺產的涉案房屋產權過戶至五人名下,每人20%份額。
馮某乙辯稱:涉案房屋系其與妻子白某的夫妻共同財產,并非遺產。
馮某甲、馮某丙、馮某丁辯稱:同意馮某戊的訴訟請求,由五人平均繼承涉案房屋。
法院經審理查明,馬某與馮某系夫妻,二人育有馮某甲、馮某乙、馮某丙、馮某丁、馮某戊五位子女。1980年馮某去世,2010年馬某去世,生前均未留遺囑。馬某自2002年至去世前一直居住在810號房屋,該房屋系馮某乙于2000年購買,2001年取得房屋所有權證,馮某乙自2002年未再居住該房屋。
馮某戊、馮某丙、馮某甲、馮某丁均表示馬某與子女通過家庭會議,口頭約定使用馬某所獲拆遷款30萬元購買810號房屋。為此,馮某戊提交內容為“今收到母親購房款27萬元整,拆遷款3萬元,共30萬元;2002年8月26日;馮某乙”的收條予以佐證。馮某乙對收條真實性認可,但表示馬某只是暫時居住810號房屋,馬某住進810號房屋后,將30萬元給其,讓其買一套樓層低、最好帶電梯的房子,后馮某乙未能購買房子,已陸續還給馬某25萬元,還剩5萬元未還,馮某乙就此未提交證據。馮某戊提交拆遷貨幣補償協議證明馬某系使用拆遷款向馮某乙支付房款,同時提交馮某乙、白某與馮某己的電話錄音,用以證明馮某乙妻子白某知悉馬某購買房屋全過程以及馮某乙出具收條的原因即為把購買810號房屋的手續履行清楚。
2018年馮某乙補辦810號房屋所有權證。馮某戊表示馮某乙將810號房屋所有權證、房屋買賣契約及收據原件交給馬某,實際由馬某長期保管。馮某乙表示上述材料放在810號房屋柜子里,其需要用的時候問過馬某的孫子馮某己,馮某己說不知道,故其補辦了房本。證人甄某、李某、仉某出庭作證,表示馬某用拆遷款30萬元買了馮某乙的房。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駁回馮某戊的全部訴訟請求。馮某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判決:一、撤銷一審民事判決;二、810號房屋歸馮某戊、馮某乙、馮某甲、馮某丙、馮某丁所有,每人占20%份額;三、駁回馮某戊其他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810號房屋是否可以在繼承人之間予以分割。
一、810號房屋是否屬于馬某的遺產
雙方均認可2002年馬某入住、馮某乙搬離810號房屋,該時間點與馮某乙出具收條時間相吻合;結合電話錄音內容,可以證明30萬元購房款與810號房屋具有一定關聯,馮某乙愛人白某對此亦知情。綜合本案證據,可以認定該收條所指向購房標的應為810號房屋。另雙方均認可自2002年馬某搬入810號房屋居住直至去世,在馬某去世后多年時間里,房屋均由馬某的孫子馮某己居住使用,其間馮某乙并未提出異議。810號房屋自2002年,即出具收條當年開始至今均未由馮某乙實際控制、占有及使用,馮某乙長達數年時間里亦未對810號房屋主張權利,明顯缺乏合理性。再者,房產證及購房手續等作為房屋權屬的證明本應由房屋權利人妥善保管,而本案中房屋所有權證原件、房屋買賣契約原件、收據原件等與810號房屋相關的手續均由馮某戊方持有,并未在馮某乙處,顯然與常理相悖。綜合上述,可以認定馬某與馮某乙之間存在房屋買賣合同關系,且馬某已經支付相應款項并一直實際占有使用810號房屋。
根據《物權法》第九條第一款之規定,雖然馬某與馮某乙之間存在房屋買賣合同關系,但該房屋權屬仍然登記于馮某乙名下,即買賣合同關系成立后,馮某乙未履行房屋登記過戶手續。因此不發生房屋權屬變更的效力。雖然上述條款規定了例外情形,然而例外情形指的是在物權法定原則下,《物權法》規定的不動產物權不需要登記或者不動產物權變動不以登記作為生效要件的情形。而本案馬某與馮某乙之間屬于普通交易行為,雖屬于母子關系,但此不足以構成上述條款的例外。房屋仍屬于馮某乙所有,故而810號房屋不屬于馬某的遺產。
二、本案對810號房屋進行分割是否有法律上的理由
810號房屋不屬于馬某遺產,但因馬某與馮某乙之間存在合同關系,因此,對810號房屋是否仍然具有分割的理由,法院持肯定態度。
根據《繼承法》第三條之規定,公民的其他合法財產包括非專屬于自然人所有的、能夠移轉的財產性權益。不具有人身專屬性的合同債權即屬于此處的其他合法財產。雖然馮某乙并未履行房屋變更登記手續,但不影響該買賣合同效力。因此,應視為馬某依據合同約定,在支付完全部房屋價金后,有要求馮某乙履行過戶登記的合同權利。該合同權利屬于不具有專屬性的財產權益,在馬某去世后,應該由其繼承人享有。故本案中馬某的遺產應確定為合同債權,而非810號房屋的物權。
各繼承人有權要求債務人履行房屋變更過戶手續以完成交易。在完成交易后,各個繼承人可以實際對房產進行分割處理。從合同履行角度考量,當馮某乙將房屋由單獨所有變更為繼承人共同所有時,可視為其履行了合同義務,如此認定也簡化了合同交易關系。但本案為繼承糾紛,在確定遺產后,仍應該在各個繼承人之間對遺產進行分配。雙方當事人均未主張馬某留有遺囑,故法院確定810號房屋應由五位子女各占20%比例。應予說明的是,雖然馮某戊等當事人主張馬某屬于房屋的權利人,810號房屋屬于遺產,而法院認為該理由并不成立,但從當事人要求繼承并分割房屋的真實訴求以及減少當事人訴累的角度,應在法律規范的范圍內綜合考量本案實際情況并最大限度處理糾紛為宜。
案例注解
不動產物權變動是一個動態的復雜過程,從買受人取得占有到完成登記往往時間較長,于此期間常滋生爭議。本案系因房屋交易已交付但未登記引發的繼承糾紛,對繼承標的界定實踐中有多種不同觀點,類案裁判或脫離民事框架純家事化,或拋開家事特性純物權化或純債權化,《民法典》的出臺使得家事法回歸民法體系,因此,需要通過司法評價和確認厘清此種情形下繼承標的性質,回應實踐與理論爭議,進而對類案形成相對統一的裁判路徑。
1
房屋交易已交付但未登記情形下的繼承標的辨析
關于不動產物權變動,通說認為我國采用的是債權形式主義的登記生效模式。[1]在此模式下,不動產物權需經登記始發生物權效力。因基于法律行為發生的物權變動是物權變動的主要方式,故不動產登記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生效的要件。因此,正確認識不動產登記的法律性質是理解不動產登記在物權權屬確認作用中的前提和基礎。
(一)不動產登記的“權利推定”與“權屬確認”
我國《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依法屬于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所有權可以不登記”,第二百一十四條“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自記載于不動產登記簿時發生效力”與第二百零九條規定相銜接,具體明確了不動產物權變動生效時間。上述規定與《物權法》關于不動產登記的內容基本相同。其中,第二百零九條規定的“法律另有規定”,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本條第二款規定的依法屬于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所有權可以不登記。二是非依法律行為而發生的物權變動情形,具體指(1)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文書,人民政府的征收決定等,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的,自法律文書生效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決定等行為生效時發生效力。(2)因繼承取得物權的,自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3)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實行為設立和消滅物權的,自事實行為成就時發生效力。三是考慮到現行法律的規定以及某些物權種類的特殊性,法律沒有一概規定必須經依法登記才發生效力。[2]例如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互換等變動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而是以登記為對抗要件,地役權的設立亦作出類似規定。
依上述,我國基于法律行為發生的不動產物權變動,以登記生效為原則,登記對抗為例外,因此不動產登記簿上記載的權利人一般推定為不動產物權的所有人。需要指出的是,登記雖然在不動產物權變動中是生效要件,但登記本身并非賦權行為,債權合意等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才是物權變動的基礎,登記則標志著當事人之間旨在轉移不動產物權的權利義務關系劃上句號。因此應把不動產登記理解為當事人不動產物權發生變動的意思表示推動的結果,或者理解為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而不能把不動產物權變動解釋為行政權力的物權授權。[3]易言之,不動產登記的目的在于對不動產物權的得喪變更進行公示,為外界知曉,維護交易的穩定與安全。其雖然可以進行真實物權人的“權利推定”,但并不能片面作為“權屬確認”的依據。
(二)“物權說”與“債權說”的博弈
司法實踐中對物權登記的效力經歷了從不區分物權變動和合同行為到區分合同行為和物權變動的變化。物權變動效果能否維持而不受原因行為效力瑕疵的牽連,不僅關乎法律行為內部當事人的利益,也關乎外部第三人的利益。在當事人之間已經成立房屋買賣合同關系并實際交付的前提下,是否必須經不動產登記方能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實踐中觀點各異。
有觀點認為,在基于法律行為發生的物權變動中,當事人之間法律行為所包含的合意與登記不一致時,可依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為依據確認不動產物權的歸屬,在不存在交易第三人的情況下能夠對抗法律物權,[4]本文稱之為“物權說”。第二種觀點認為,已實際占有房屋之買受人取得的是一種介于債權向物權轉變過程中的“準物權”,交付占有后的出賣人對標的物所享有的所有權中已不再包含占有、使用、收益三項核心權能,其所有權實質上已經被掏空,[5]本文稱之為“準物權說”。第三種觀點認為,當事人關于不動產物權歸屬的約定,在以登記生效為要件的物權變動模式下,不具有物權法上的效力,不符合物權變動生效要件,其性質為債權而非物權,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應基于合同約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加以處理。[6]本案的裁判采納了后者觀點,筆者認為,不動產登記在本質上雖然是不動產物權的公示方式,但對其性質的認識不能脫離法律賦予不動產登記生效要件的法律地位這一基礎。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物權的種類和內容,由法律規定。由此明確了我國物權法定的基本原則。對于物權法定原則的含義,理論上有不同看法。法國學者所解釋的物權法定,僅指物權類型和內容的限制,而德國學者所解釋的物權法定,則不僅包括物權類型和內容的限制,而且還包括物權設立和移轉形式的限制。至于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對其立法上明文規定的對法定物權外的物權的“創設”的禁止規定中之“創設”的理解,則均認為是對物權種類和內容之任意創設的限制。[7]筆者認為,物權的移轉由法律規定,而不能由當事人自由創設是物權法定這一基本原則的應有之義。“物權說”雖然在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等以登記對抗為原則的不動產物權變動時在結論上是成立的,但實際上混淆了物權與債權的概念,與我國物權法規定的物權變動的主要模式和要件在根本上相違背,其將導致虛化不動產登記在物權變動中的法律作用或效力的后果。應當認為,我國不動產物權變動同時需要法律行為和依法登記,雙重法律事實決定不動產物權變動的效力。[8]若僅具有當事人之間的原因行為,而未完成登記,則相應的物權變動因欠缺生效要件而未發生物權效力。
結合本案證據及雙方當事人陳述可以認定馬某與馮某乙之間存在房屋買賣合同關系,馬某已支付完全部價款并實際占有使用房屋,但在房屋未完成權屬變更登記的情況下,房屋所有權仍應為出賣人馮某乙所有,馬某僅享有要求馮某乙履行過戶登記的權利。在馬某去世后,繼承標的應為債權,而非物權。
2
房屋買賣合同相對人死亡后權利義務的承繼
一般而言,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約束力,而本案中房屋買賣合同的買受人一方在履行完支付全部價款的義務后去世,出賣人一方過戶登記的義務尚未履行。此時,繼承能否突破合同相對性原則,由繼承人承繼買受人的權利系本案的另一焦點。此問題解決的前提是確定合同債權能否納入遺產的范疇。
(一)繼承人基于合同成立且已部分履行而承繼買受人的權利
遺產作為繼承的客體,經過了一個從身份權逐漸式微與財產權日益擴張的演化過程。我國《繼承法》第三條對遺產范圍的規定采納了“正面概括加列舉”的模式,以“公民的其他合法財產”作為兜底條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條對該兜底條款進一步明確為“公民可繼承的其他合法財產包括有價證券和履行標的為財物的債權等”。由此可見,法律將部分債權納入遺產的范疇之中。
隨著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變化,財產權利不斷增添新的內容,遺產范圍采用列舉的方式難免會存在立法漏洞,進而增加法律被修改、補充的可能,不利于法的穩定性,因此,《民法典》放棄列舉的方式,將“正面概括加反面排除”模式作為立法的選擇。《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四條對繼承權作出規定“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財產,可以依法繼承”,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對遺產范圍進行明確“遺產是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根據其性質不得繼承的遺產,不得繼承”。對遺產的排除范圍可從兩方面予以界定,一是依照法律規定不得繼承的不得作為遺產,包括自然資源利用權、宅基地使用權、生前租用或借用他人的財產、指定了受益人的保險金等;二是根據其性質不得繼承的除外,主要指與被繼承人人身有關的專屬性債權。[9]這種模式大大拓展了遺產的范圍,將現有財產如物權、債權、知識產權、股權等全部納入其中,而且為網絡虛擬財產權等已經出現或未來可能出現的新型數據財產權等留足了空間。
依上述,無論是本案裁判時所依據的《繼承法》還是現已施行的《民法典》均將債權納入遺產的考量范疇,即除與被繼承人人身有關的專屬性債權或合同特別約定不得繼承的債權外,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其他合法債權應作為遺產進行繼承。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繼承只是對合同中規定的債權的繼承,而并非對合同本身的繼承,除了合同中特別約定的以外,繼承人不能因被繼承人的死亡而當然取代被繼承人成為合同的當事人。
本案中馬某生前與馮某乙訂立房屋買賣合同并已依約履行合同義務,其去世時遺留的對馮某乙的合法債權可由其繼承人進行承繼,即其繼承人可要求馮某乙繼續履行過戶登記的義務。
(二)繼承人與出賣人身份重合時合同義務的履行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馮某乙既為房屋買賣合同的出賣人應依約履行義務,又系法定繼承人之一可承繼馬某去世時遺留的合同權利,身份的重合導致本案債務應向誰履行、如何履行存在一定障礙。考慮被繼承人已經去世,權利主體資格消滅無法繼續承受權利,若要求義務人繼續過戶給被繼承人顯然不合宜,結合上述繼承人可依法繼承部分合法債權的闡述,本案裁判認為當繼承人與義務人身份重合時,義務人(同時也是繼承人之一)向其他繼承人履行合同義務即可視為其合同義務已履行完畢,此種做法便利當事人訴訟的同時也提高了爭議解決的效率。具體到本案中,當馮某乙將房屋由單獨所有變更登記為繼承人共同所有時,即可視為其履行了合同義務。
3
本案基于合同債權在繼承糾紛中一體化處理的考慮
前述分析繼承人可以對被繼承人死亡時遺留的合同權利進行承繼,但是否能在本案中對合同履行與繼承分割一并處理實踐中尚有爭議。
一種觀點認為,繼承人雖然可以承繼合同權利,但應由被繼承人馬某的其他繼承人首先起訴馮某乙繼續履行合同,將涉案房屋由馮某乙單獨所有變更為繼承人共同所有后,再起訴繼承糾紛對房屋比例進行具體的分割。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本案系繼承糾紛,在確定被繼承人馬某遺留的合同債權可以繼承后,可以一并處理合同履行、遺產繼承和房屋分割三個問題。
本案裁判采納了后者觀點,主要出于以下方面考慮:首先,本案連帶處理合同履行與遺產繼承于法有據。要求馮某乙過戶登記系被繼承人馬某去世時遺留的合法債權,債權作為自然人一項重要的財產權利,其繼承人有權承繼,即要求馮某乙向其他繼承人繼續履行合同義務。其次,繼承并分割房屋系本案當事人的真實訴求。馬某的繼承人起訴本案的直觀訴求并非要求確認房屋為所有繼承人共同共有,而是對房屋份額進行具體分割。若按照第一種觀點,法院至多只能在裁判文書說理部分對被繼承人遺留的合法債權可以承繼進行釋明,但對當事人要求繼承分割房屋的訴訟請求因需待其另行訴訟合同履行后方能裁判,故本案只能作出駁回當事人訴求的裁判結果,這不僅與當事人訴求不相符,亦與減少當事人訴累的司法精神不相合。最后,本案對合同債權在繼承糾紛中一體化處理系個案衡平與類案統一司法要求的應有之義。本案涉及物債兩分的辨析、合同履行與權利繼承的沖突、繼承人與義務人身份的重合等多項復雜而特殊的問題,在統一類案司法適用的基礎之上,更應在法律規范的范圍內綜合考量本案實際情況并最大限度處理糾紛為宜,故本案最終采納后者觀點,對合同債權的承繼在繼承糾紛中一體化處理。
注釋
來源: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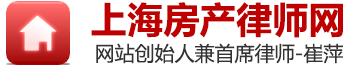


 滬公網安備31010702006145
滬公網安備3101070200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