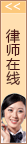直接要求以唯一繼承人身份主張繼承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權益的正確認定
來源:上海房產律師網 作者:上海律師 時間:2021-09-10
裁判要旨
當事人主張享有被繼承人因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而產生的財產權益,當事人應證明其為被繼承人的唯一合法繼承人。涉及養子女或遺囑繼承的,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規定審查,但對于當事人基于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訴求安置方履行協議、分配房屋的,不宜對繼承糾紛一并審理。當事人應先通過另案繼承糾紛確定其為被繼承人唯一合法繼承人后,再行主張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權益。
基本案情
原告商某乙向人民法院起訴稱:商某甲系被告某村民委員會村民,在該村享有一切村民待遇,位于某村院落及房屋一處系商某甲所有。原告商某乙系商某甲的養女,2013年10月11日被告某村民委員會與商某甲簽訂《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該協議第三條約定:經某房地產評估有限公司評估補償價值共計117177元。第八條約定:每戶分兩套樓房,一套約120-130平方,二套約90平方。2013年3月9日被告出臺村房屋拆遷安置分配方案,第二條規定:“祖籍是本村,戶口在本村,并長期居住的,享受村民待遇的男性公民或妻子,有獨立宅基房產,是村集體經濟成員的戶,及有女無子、已結婚的養老女婿或女兒已滿十八周歲,有宅基地的享受安置房、保障房各一套”。被告某村民委員會一直給原告商某乙按商某甲女兒身份享受村民待遇(有股權證等),并且原告也為商某甲養老送終,盡到了女兒的贍養義務。請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按照該村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及房屋拆遷安置分配方案為原告分配安置房(約130平方米)、保障房(約90平方米)各一套,上述兩套房屋價值約700000元,被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被告某村民委員會辯稱:一、原告主體不適格。原告不是安置協議的合同相對方和宅基地的所有人,不具有作為原告的主體資格。二、原告主張的養女身份缺乏有效法律文件的確認,原告主張系商某甲養女依據不足。三、原告的主張屬于繼承權法律關系,不屬于本案的審理范圍。請求依法駁回原告的起訴。
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13年,被告某村民委員會組織進行舊村改造,并制定《拆遷安置分配方案》,該方案第二條規定:“祖籍是本村,戶口在本村,并長期居住的,享受村民待遇的男性公民或妻子,有獨立宅基房產,是村集體經濟成員的戶,及有女無子、已結婚的養老女婿或女兒已滿十八周歲,有宅基地的享受安置房、保障房各一套。”2013年10月11日,被告與商某甲簽訂《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載明商某甲宅基地及房屋評估補償價值共計117177元,又載明各戶的安置執行《舊村改造房屋拆遷安置分配方案》,新居每戶兩套,面積一套為120-130平方米,二套約90平方米,老年公寓70-80平方米。該協議另對其他事項進行了約定,但由商某甲、馬某某共同簽名。
另查明,商某甲在某村宅基地為2組150號,商某甲有兄弟四人,其兄為商某丙,商某丁,其弟為商某戊。原告商某乙非商某甲生女,其戶口在原告商某乙生母馬某某戶下。原告主張其為商某甲養女。2011年商某甲訴商某乙贍養糾紛一案,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雙方協議由商某乙自2010年12月21日起對商某甲承擔相關贍養義務,商某甲全部家庭財產由商某乙享有。原告提供商某甲2018年9月8日遺囑一份,遺囑中商某甲表示去世后一切財產由商某乙繼承,置換的房屋由商某乙一人繼承。原告提供的商氏族譜中商某乙為商某甲“嗣女”,商某戊名下商某乙為“出嗣”。商某甲于2018年9月去世。
某村舊村改造,2019年第一批新房建成并于2020年分配,第一批大部分村民已分配完畢。商某甲舊房屋尚未拆除。原告結婚后,居住于臨淄區西高生活區,共戶口在某村,仍屬某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裁判結果
人民法院判決:駁回原告商某乙的訴訟請求。一審判決作出后,雙方均未上訴。
案例解讀
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條規定: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規定:遺產是指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依照法律規定或者根據其性質不得繼承的遺產,不得繼承。依照法律規定不能繼承的財產權利主要包括自然資源利用權、宅基地使用權、生前租用或借用的他人的財產、指定了受益人的保險金等;依據權利性質不得繼承的財產主要是指與被繼承人人身有關的專屬性債權。本案中,商某甲與某村民委員會簽訂了《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依據該村《舊村改造房屋拆遷安置分配方案》,商某甲享有的安置房、保障房各一套屬于因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產生的債權(財產權利),商某甲的繼承人繼承的是該債權,不是合同關系的繼承,不屬于上述不得繼承的情形。
本案中,商某甲和與商某乙是否具有收養關系,是認定商某乙是否具有繼承權的基礎。原告商某乙以商某甲養女的身份主張權利,對于養子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條規定:自收養關系成立之日起,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本法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第一千一百零五條規定:收養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收養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原告商某乙未能提交收養登記證明,雖然其提供了民事調解書,但對于民事調解書是否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三條規定中的“裁判”,相關的法律與司法解釋尚未予以明確規定,故司法實踐不宜對其進行擴大解釋;同時,民事調解實質上是當事人對自己私權利的處分,其功能主要是減少訟累、定分止爭,與法院判決不同的是其對事實的認定很大程度上偏重于雙方當事人的自認,在不違反強制性法律規定的前提下,調解所確認的事實和法律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的合意,調解書的形成過程往往局限于案件的雙方當事人,缺乏另案相關當事人的參與,因此已經生效的民事調解書對另案的事實認定并不當然具有絕對的預決力。原告商某乙提供的家譜、遺囑等證據,均不能代替民政部門的登記。且本案尚涉及在收養法之前還是之后雙方形成收養的問題。因此,原告未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能認定收養關系成立的有效證據。
商某甲原親兄弟共四人,商某甲戶口與孫某某同戶,原告商某乙戶口與其生母馬某某同戶,涉案的商某甲的原房屋及以后應分配的房屋,是否還有其他共有人,本案中不能確定。原告所主張的兩套房屋,只有一套安置房已建設完畢,第二批房屋尚未建設。本案還涉及能否在該案一并審理繼承糾紛問題。繼承糾紛系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關于遺產繼承的糾紛,涉及繼承人一人或多人。對于繼承人的資格、遺囑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以及遺產如何分配等,需由繼承糾紛解決。對此,《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繼承編的解釋(一)》均作出明確規定。而本案原告主要訴請系要求被告履行協議、分配房屋,因當事人不同,案由不同,故不宜同時審理繼承糾紛。因此,法院認定原告直接起訴主張涉案拆遷安置補償協議中的權益證據不足,不予支持。原告應先通過另案繼承糾紛明確其唯一繼承人身份后再行解決其本案主張。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五條 收養應當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收養關系自登記之日起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條 遺產是指自然人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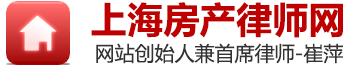


 滬公網安備31010702006145
滬公網安備31010702006145